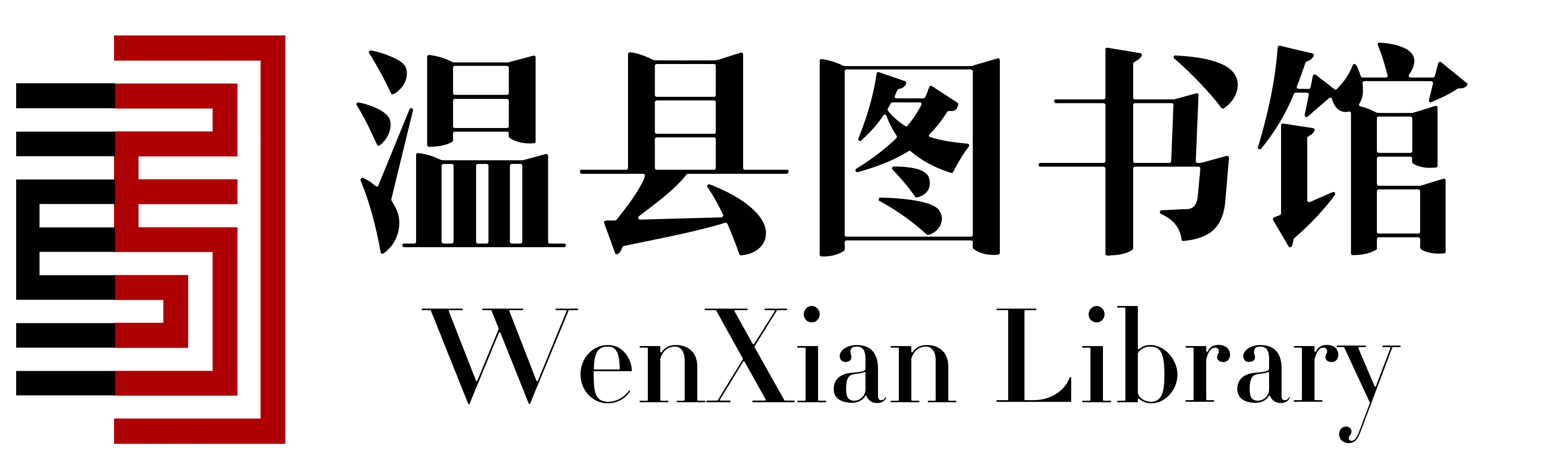《白鹿原》:注定是一部要改變當代文學史叙事結構的(de)作品
本期是“作家論·陳忠實專題”最後一篇。雷達、何平、李建軍三位評論家,分(fēn)别從對(duì)曆史的(de)把握、對(duì)人(rén)性的(de)挖掘與呈現、對(duì)現實主義創作的(de)開掘等方面,對(duì)作家陳忠實及其創作進行闡釋和(hé)研究。經典闡釋具有無限性,希望這(zhè)組評論對(duì)于當下(xià)創作有所啓發。
——編 者
核心閱讀
陳忠實認識到了(le)曆史與小說的(de)密切關聯,我們從他(tā)的(de)叙事中看到了(le)真實的(de)曆史和(hé)真實的(de)人(rén)
一個(gè)作家的(de)偉大(dà),很大(dà)程度上體現在對(duì)善的(de)正确理(lǐ)解和(hé)深刻表達上,陳忠實寫出了(le)民族道德和(hé)倫理(lǐ)中不滅的(de)善,我們從中看到了(le)他(tā)慈悲的(de)仁者形象
《白鹿原》既吸納現代小說的(de)叙事技巧,也(yě)用(yòng)心追求現實主義小說在細節描寫上的(de)準确性和(hé)真實性,塑造了(le)一大(dà)批過去未曾有過的(de)人(rén)物(wù)形象
時(shí)間是文學品質和(hé)價值最可(kě)靠的(de)試金石和(hé)顯影(yǐng)劑。《白鹿原》就是一部經受住了(le)時(shí)間考驗的(de)傑作。即使相隔20多(duō)年,回頭看,它仍然是令人(rén)震撼的(de)文學奇迹,依然是一部偉大(dà)的(de)文學傑作。
陝西人(rén)常用(yòng)“咥冷(lěng)活”形容一個(gè)人(rén)幹了(le)件出人(rén)意料的(de)事情。然而,誰也(yě)沒有想到,陳忠實會“咥”這(zhè)麽大(dà)一個(gè)“冷(lěng)活”,會寫出這(zhè)樣一部金聲玉振、不同凡響的(de)長(cháng)篇小說。
《白鹿原》注定是一部要改變當代文學史叙事結構的(de)作品。它不僅徹底改變了(le)陳忠實自己的(de)作家形象和(hé)文學地位,而且也(yě)在很多(duō)方面,将當代長(cháng)篇小說的(de)寫作水(shuǐ)平提升到了(le)一個(gè)嶄新的(de)高(gāo)度。
一部繼往開來(lái)的(de)現實主義巨著,深刻理(lǐ)解所叙寫的(de)曆史與人(rén)
《白鹿原》是一部亦因亦革、繼往開來(lái)的(de)現實主義巨著。它以多(duō)方面的(de)成功,證明(míng)了(le)現實主義文學不僅具有自我更新的(de)活力,而且還(hái)擁有無限廣闊的(de)前景。
就創作态度和(hé)創作方法來(lái)看,陳忠實像路遙一樣,沒有被甚嚣塵上的(de)文學“新風潮”所迷惑和(hé)裹挾,也(yě)從來(lái)沒有喪失對(duì)現實主義文學的(de)信心。創作這(zhè)樣一部小說,既需要成熟的(de)文學意識和(hé)文學經驗,也(yě)需要不爲時(shí)風所移的(de)冷(lěng)靜和(hé)清醒。
陳忠實的(de)成功,首先取決于他(tā)能“轉益多(duō)師”,虔誠而虛心地學習(xí)多(duō)種模式和(hé)風格的(de)現實主義文學的(de)經驗。他(tā)始終珍惜并學習(xí)柳青的(de)文學經驗,先後買過許多(duō)本《創業史》,無數次研讀這(zhè)部藝術性很高(gāo)的(de)傑作。對(duì)柳青來(lái)講,觀察先于想象,身曆目見是小說家必須跨過去的(de)鐵門檻;他(tā)更相信自己眼睛,更注重對(duì)生活和(hé)人(rén)物(wù)的(de)深入而細緻的(de)觀察,而不是關起門來(lái)憑著(zhe)才氣任意揮灑,憑著(zhe)天馬行空的(de)想象随意杜撰。觀察需要付出切實的(de)努力,來(lái)不得(de)半點馬馬虎虎的(de)偷懶,所以,柳青才說“文學是愚人(rén)的(de)事業”。陳忠實像柳青一樣,按照(zhào)最老實的(de)方式來(lái)寫小說。如果說,路遙從柳青那裏學來(lái)了(le)抒情化(huà)的(de)叙述方式,那麽,陳忠實則掌握了(le)柳青細緻、準确、傳神的(de)描寫技巧。像柳青一樣,陳忠實筆下(xià)的(de)人(rén)物(wù),也(yě)是使用(yòng)錾子在生活的(de)石頭上一下(xià)一下(xià)鑿出來(lái)的(de),幾乎個(gè)個(gè)都給人(rén)一種雕塑般的(de)堅實感。
陳忠實還(hái)從巴爾紮克和(hé)哈代的(de)長(cháng)篇小說中、從契诃夫和(hé)莫泊桑的(de)短篇小說中、從《靜靜的(de)頓河(hé)》《憤怒的(de)葡萄》《碧血黃(huáng)沙》《百年孤獨》和(hé)《假如明(míng)天來(lái)臨》等多(duō)種樣态的(de)外國現實主義小說作品中,理(lǐ)解了(le)人(rén)與曆史的(de)關系,吸納了(le)新鮮的(de)叙事技巧,領悟到了(le)解決可(kě)讀性的(de)方法,從而使《白鹿原》成爲一部既傳統又現代、既莊嚴又親切、既有思想性又有可(kě)讀性的(de)偉大(dà)作品。
小說是人(rén)類生活别樣形态的(de)曆史。然而,曆史感的(de)喪失,卻是當代小說叙事的(de)一大(dà)危機。一些小說家的(de)叙事是封閉而蒼白的(de),是沒有背景的(de)——既沒有現實背景,也(yě)沒有曆史背景。他(tā)們筆下(xià)的(de)人(rén)物(wù)與故事,皆如飄忽的(de)影(yǐng)子,忽焉而來(lái),忽焉而去,仿佛無本之木(mù),隻有枝葉,沒有根系,缺乏清晰的(de)來(lái)路和(hé)内在的(de)深度。
然而,陳忠實認識到了(le)曆史與小說的(de)密切關聯。沒有曆史的(de)生活是不完整的(de),沒有曆史的(de)人(rén)物(wù)是不真實的(de),小說可(kě)以被理(lǐ)解爲“民族的(de)秘史”。這(zhè)是更真實的(de)曆史,是小說家需要深入理(lǐ)解和(hé)叙述的(de)曆史。陳忠實通(tōng)過閱讀、調查和(hé)思考,深刻地理(lǐ)解了(le)他(tā)所叙寫的(de)曆史生活,理(lǐ)解了(le)處于特定曆史語境中的(de)人(rén)。
在他(tā)的(de)理(lǐ)解中,曆史不再是僵硬的(de)公式化(huà)表述,人(rén)也(yě)不再是曆史幹巴巴的(de)填充物(wù),而是有血有肉的(de)複雜(zá)生命體。他(tā)寫出了(le)真實的(de)曆史,也(yě)塑造出了(le)真實的(de)人(rén)物(wù)形象。他(tā)們有愛(ài)恨與情仇,有沖突與和(hé)解。《白鹿原》中的(de)曆史,就是真正屬于人(rén)的(de)曆史;其中的(de)人(rén)和(hé)人(rén)之間的(de)相互沖突,是豐富的(de)人(rén)性以及複雜(zá)的(de)關系引發的(de)沖突,而不再是某種觀念抽象的(de)沖突。
《白鹿原》在人(rén)性的(de)意義上,超越了(le)非人(rén)性叙事的(de)狹隘性;在真實性的(de)意義上,克服了(le)教條的(de)曆史意識的(de)虛假性。我們從他(tā)的(de)叙事中看到了(le)真實的(de)曆史和(hé)真實的(de)人(rén)。
一部倫理(lǐ)現實主義作品,寫出我們民族道德倫理(lǐ)中永遠(yuǎn)不滅的(de)善
文學既是美(měi)學現象,也(yě)是倫理(lǐ)現象。倫理(lǐ)精神是人(rén)們評價一部文學作品的(de)重要尺度。偉大(dà)的(de)作品首先是指那種在倫理(lǐ)精神上達到很高(gāo)境界的(de)作品。美(měi)好的(de)道德詩意和(hé)倫理(lǐ)光(guāng)輝,是一部偉大(dà)的(de)作品最能吸引人(rén)和(hé)打動人(rén)的(de)内在力量。
一個(gè)作家的(de)偉大(dà),很大(dà)程度上就體現在對(duì)善的(de)正确理(lǐ)解和(hé)深刻表達上。如果說路遙的(de)寫作充滿了(le)青春的(de)激情,表現了(le)他(tā)個(gè)人(rén)的(de)經驗以及時(shí)代的(de)經驗,彰顯了(le)陷入逆境的(de)個(gè)人(rén)應該具有的(de)美(měi)好德行、堅韌意志和(hé)奮鬥精神,那麽,陳忠實就憑著(zhe)自己成熟的(de)理(lǐ)性,表現了(le)我們民族漫長(cháng)曆史中的(de)苦難,以及擺脫這(zhè)種苦難應該選擇的(de)方向、應該有的(de)道德精神。就此而言,《白鹿原》屬于倫理(lǐ)現實主義文學的(de)範疇。
陳忠實寫出了(le)我們民族道德和(hé)倫理(lǐ)中永遠(yuǎn)不滅的(de)善。《白鹿原》在倫理(lǐ)精神上真正吸引我們、打動我們的(de)東西,就是這(zhè)種善。在《白鹿原》裏,人(rén)的(de)内心充滿了(le)道德痛苦和(hé)道德焦慮,而整個(gè)小說就在兩種倫理(lǐ)文化(huà)沖突中展開:一種新的(de)文化(huà)進來(lái)了(le),它有理(lǐ)想,有激情,對(duì)生活要有新的(de)安排;而舊(jiù)的(de)文化(huà)、道德精神則處于守勢,面臨被新的(de)文化(huà)和(hé)道德解構掉的(de)命運。
《白鹿原》打動我們的(de),就是那些将要失去精神家園、失去未來(lái)的(de)人(rén)物(wù)身上的(de)道德光(guāng)輝和(hé)道德激情。無論是一心向學問道的(de)鄉賢朱先生,還(hái)是總是嚴正凜然的(de)族長(cháng)白嘉軒,還(hái)是永遠(yuǎn)忠誠厚道的(de)鹿三,都不是不食人(rén)間煙(yān)火的(de)道德超人(rén)。他(tā)們也(yě)有七情六欲,也(yě)犯一些常人(rén)都犯的(de)錯誤,但是,在他(tā)們的(de)内心深處,良心之火從未熄滅。他(tā)們有情有義,敢于擔當。陳忠實懷著(zhe)非常強烈的(de)感傷寫出了(le)這(zhè)樣的(de)悲劇結局:原上最後一個(gè)好先生、最後一個(gè)好長(cháng)工、最後一個(gè)好地主,都消失了(le)。這(zhè)是他(tā)站在當下(xià)的(de)基點上回望曆史時(shí)候的(de)感受,也(yě)表現著(zhe)他(tā)在曆史中觀照(zhào)現實的(de)焦慮。
一座将人(rén)物(wù)置于中心位置的(de)文學高(gāo)峰,同時(shí)體現出作家智者與仁者的(de)形象
就藝術性來(lái)看,《白鹿原》足以代表當代現實主義長(cháng)篇小說創作的(de)最高(gāo)水(shuǐ)準和(hé)最高(gāo)成就。幾十年來(lái),沒有哪部長(cháng)篇小說能給人(rén)們帶來(lái)如此強烈的(de)美(měi)學震撼和(hé)如此豐富的(de)藝術享受。
叙事是小說的(de)重要技巧,但不是小說價值構成的(de)主體部分(fēn)。叙事的(de)最終目的(de)在塑造人(rén)物(wù)。塑造人(rén)物(wù)才是小說藝術的(de)根本任務。一部小說倘若沒有塑造出能讓人(rén)記住甚至讓人(rén)迷戀的(de)人(rén)物(wù),那它就很難說是一部好小說。
現代小說的(de)危機很大(dà)程度上就體現在人(rén)物(wù)被叙事淹沒這(zhè)一方面。衆所周知,20世紀80年代以來(lái),随著(zhe)對(duì)傳統的(de)現實主義文學經驗的(de)排斥和(hé)對(duì)“現代主義”的(de)認同,小說作者的(de)主觀和(hé)任性被當作一種先鋒姿态;小說寫作陷入了(le)叙事壓垮描寫、作者遮蔽人(rén)物(wù)的(de)誤區(qū)裏;小說中充滿了(le)花樣翻新的(de)技巧實驗和(hé)話(huà)語狂歡,但缺乏真實可(kě)信的(de)細節描寫和(hé)個(gè)性飽滿的(de)人(rén)物(wù)。
《白鹿原》撥亂而反正之,既吸納了(le)現代小說的(de)叙事技巧,也(yě)用(yòng)心追求現實主義小說在細節描寫上的(de)準确性和(hé)真實性,并将人(rén)物(wù)置于小說世界的(de)中心位置。它調動了(le)隐喻、象征等多(duō)種修辭技巧,塑造了(le)一大(dà)批栩栩如生、令人(rén)難忘的(de)人(rén)物(wù)形象。他(tā)給當代文學的(de)人(rén)物(wù)畫(huà)廊貢獻了(le)一系列嶄新的(de)人(rén)物(wù)形象:朱先生、白嘉軒、鹿子霖、田小娥、白孝文、鹿三、黑(hēi)娃,幾乎個(gè)個(gè)都是過去未曾有過的(de)人(rén)物(wù),都有著(zhe)屬于自己的(de)氣質和(hé)個(gè)性。
如何塑造女(nǚ)性形象,能夠檢驗一個(gè)作家的(de)精神高(gāo)度。在對(duì)女(nǚ)性形象的(de)塑造上,陳忠實的(de)作品表現出一種現代性的(de)教養。他(tā)寫到了(le)她們的(de)不幸,同情她們的(de)悲慘遭遇,并代她們發出了(le)抗議(yì)的(de)聲音(yīn)。陳忠實對(duì)女(nǚ)性悲劇命運的(de)表現是深刻的(de),充滿了(le)現代的(de)啓蒙意識和(hé)批判精神。尤其是田小娥這(zhè)一形象,蘊含著(zhe)豐富的(de)人(rén)性内容和(hé)文化(huà)内容,也(yě)具有豐富的(de)象征意味。威爾遜将《日瓦戈醫生》中的(de)拉拉當作俄羅斯民族的(de)象征,某種程度上,田小娥也(yě)具有一定的(de)象征意義。
作者形象是小說的(de)形象譜系構成中極爲重要的(de)部分(fēn),與人(rén)物(wù)形象有著(zhe)同樣重要的(de)地位和(hé)作用(yòng)。人(rén)與文是相通(tōng)的(de),什(shén)麽樣的(de)人(rén)寫什(shén)麽樣的(de)小說。小說是一個(gè)作家秘密的(de)人(rén)格檔案,而且是他(tā)非常可(kě)靠的(de)人(rén)格鏡像。一個(gè)偉大(dà)的(de)小說家都會在塑造人(rén)物(wù)形象的(de)同時(shí),塑造一個(gè)真實的(de)自我形象。人(rén)們透過小說作品,可(kě)以看到作者自己的(de)情感态度、人(rén)格狀況和(hé)思想境界。
《白鹿原》中的(de)作者形象,是一個(gè)穎悟的(de)智者,一個(gè)慈悲的(de)仁者。他(tā)危懼悲吟,凄涼在念,内心充滿了(le)對(duì)人(rén)間不幸的(de)同情和(hé)憐憫,對(duì)美(měi)好事物(wù)和(hé)美(měi)好德行的(de)真誠熱(rè)愛(ài)和(hé)贊美(měi)。他(tā)的(de)小說是白鹿原上種種人(rén)物(wù)的(de)苦難史,但也(yě)是作者獻給那些逝者的(de)安魂曲,獻給生者的(de)充滿善意和(hé)智慧的(de)啓示錄。他(tā)希望同胞們能從自己的(de)作品裏獲得(de)積極的(de)生存智慧,在未來(lái)活得(de)更理(lǐ)性、更道德、更幸福。我們從《白鹿原》中,看到了(le)陳忠實健全的(de)人(rén)格和(hé)善良的(de)心性——他(tā)塑造了(le)一個(gè)真實而美(měi)好的(de)自我形象。
總之,無論從作品的(de)美(měi)學價值和(hé)藝術旨趣上看,還(hái)是從它所表現的(de)作者的(de)倫理(lǐ)自覺和(hé)人(rén)格境界上看,《白鹿原》都是一部偉大(dà)的(de)作品。它代表著(zhe)當代長(cháng)篇小說創作的(de)最高(gāo)成就,是一座真正的(de)文學高(gāo)峰。李建軍
(作者爲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(yuán))